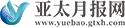◼️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法兰克福学派学者洛文塔尔在《大众偶像的胜利》一文中对社会中所存在的为人瞩目并追捧的对象作出讨论,认为在“生产偶像”逐渐落寞并退出核心聚光灯之后,来自于娱乐工业领域,主推为大众创造出更多梦想寄托和情感陪伴、资本售卖的“消费偶像”正成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被重新定义的公众角色。
◼️ 所谓「大众偶像的胜利」与对公共视线的进一步占领,实际上标志着社会运作与机器运转的核心路径正逐渐脱离生产力、生产效能的快速提升,反之,它关注的是如何促进市场消费与文化发展,调动来自公众群体对商品的购买能力。这也与鲍德里亚所辨析的消费社会的观点如出一辙,无论是从视觉上,还是来自人格魅力的包装与扮演,通过无数景观的精心设计,打造出符合不同时代特征与需求的偶像。他们/她们如同货架上的商品,通过售卖姣好的长相、动听的声音,或是使人共情的演技,获得受众粉丝的追捧,实现价值变现。
 (相关资料图)
(相关资料图)
◼️ 而当这一境况在被视觉化的网络媒介技术无限放大后,便来到了七八年前从港台明星、韩国明星逐渐回归到内地的时候,文娱业一片向好,选秀节目、电视电影捧红了一众偶像,又通过粉丝群的维护、周边与各式各样的产品售卖赚得盆满钵满。那是一个把握住所谓顶流明星,便可以轻易拿个上亿票房、博得收视高峰的时代。另一方面,深谙偶像与粉丝逻辑的文娱产业野心根本不至于此,他们既要推出一个又一个顶流,也要培养饭圈思维,创新出所谓“妈粉”文化,以打投、票选的方式,用哺育、扶持的粉丝角色代偿,不断聚拢分散的追星人,形成有组织、有黑话、有规则的饭圈社群,实现自给自足、持续创造新收益的文娱形式。
◼️ 所以,这块大众偶像的蛋糕越做越大,饭圈的逻辑渗透向其他不同的公共领域范畴中去:体育界、小说家、短视频网红,乃至政治外交官、国家象征,都有了属于自己的粉丝后援队伍。彼时,问题也不断出现——社交媒体允许用户参与进内容实践的范畴中来,也同样将所谓偶像与素人的距离无限缩小——会发疯的女明星、会睡粉的男明星、会吐痰会抽烟的青年偶像、会口吐脏话的可爱花旦、读错字的文化人。
◼️ 明星前台与后台在公私域的模糊下快速崩塌,三天两头就是律师函与不冷不热的官宣声明。小戏码公众早已看腻,心理底线不断被破降低,大戏码也逐渐见惯不怪,进去踩缝纫机的、一夜之间全网销声匿迹的,都成了震惊之余的饭后谈资。此外,要演技有瞪眼、要综艺有借鉴、要搞笑有架子、要题材有古偶,也都成了如今这娱乐圈的标配。
◼️ 如此看来,这内娱,一定还有救(愚人节玩笑版)!
04/01/Sat.
我应该是得了
吃瓜倦怠综合症。
@TuTouSuo™️
临近中午时睁眼,社交媒体里便适时地跳出若干条消息,都是关于同一个众人耳熟能详的名字,一位在我高中时就看过他比赛的运动员的爆料赫然出现在热搜榜榜首,与之相提的,是他的前女友,同样是近几年文娱领域里较有国民知名度的明星。
可惜,这俩人我一个都不关心——即使有学者通过核磁共振技术发现个人在吃瓜的时候大脑的奖励中枢会被显著激活,创造愉悦的快感。很显然,在这几年轮番横跳在瓜田周围来回品味一个又一个“塌房”选手荡气回肠的塌房故事,无论是借腹生子、触犯法律,还是悄默声地生了个娃、结了个婚,内娱在社交媒体上可谓是天天都有新花样,已然将作为吃瓜群众的我的底线一再拉低,甚至产生了对这群偶像明星们的抵触心理:
家长里短的事,别再上热搜了。
当然,除了这些让人耳朵生茧的爆料、律师函、要锤得锤等系列行动带来的吃瓜倦怠综合症之外,我也在内娱的天地里发现更多新鲜的变化。
例如“少操心208万们的生活,怎么过得也比你舒服”;“明星真的越来越廉价,不如承认自己就是个网红”;“求别营销人设,私底下难道不是烟酒都来吗”;“姐,你是我唯一的姐!”。
据我观察,如此大多数的现象都是在近五年的时间里广泛出现的,尤其是在屡次爆出明星天价薪酬、偷税漏税,以及一大波曾经的演员、歌手开始直播带货后,更是使众人对这些往日看起来光鲜、不可触碰的角色开始“祛魅”,甚至在阶层分化明显、贫富差距扩大、饭圈成为治理对象,群体仇富与仇权观念越发强烈的当下,催生出更为偏激的言论,对饭圈、对明星偶像的舆论导向也变得更加尖锐,群体对立的风险持续增加。
或许许多被称为「路人」角色的公众,都会在当前的内娱市场中感到某种倦怠和无聊,厌烦参与到每一场的「饭圈罗生门」里,一边看着粉丝内部来回争吵,一边在其中试图摸索出可能的事件真相。最后只落得个什么也看不明白,白瞎一整天的结果。
但也正是一次次的吃瓜,让公众如大梦初醒般发现,实际上所谓的明星、偶像,与自己也并未有几分不同,同样有七情六欲,同样会拉屎放屁。
将近一百年后的大众偶像已不再是洛文塔尔口中简单的促进公众花销与理想崇拜的“消费偶像”,他们正在从大众媒介以垄断的话语资源所筑成的神坛上跌落,变成无时无刻受到公众监督,仅仅离普通人一岸之隔的角色。
他们更需要的,不再仅仅是一张漂亮的脸蛋或营销某些人设,更是要有实际的能力,使其能够说服观众:
这是我的职业,是一个需要专业技能的行业。
由此才能构建起更完整的、坚固的职业合法性。
@TuTouSuo/2024
◼️ 扁平化的技术中介
◼️ 创造出了下沉的偶像景观
在谈到大众偶像时,其符号指称对象天然地与二十来年前具有垄断性质的电视与广播、报纸等大众媒介相互联系。前者依托于后者的传播渠道,后者也通过其自身所天然携带的社会权威与稀缺性质,为偶像的定义赋权,构建出他们万一挑一的绝对地位。再加上剧集、综艺制作资源有限,行业内部竞争性较强,除了业务能力突出的对象,其他都只能沦为陪衬,继续钻研磨砺,提升自己的实力。
如果说网络媒介的出现使传统电子媒介的传播资源被迫分割和下放,那么建基于大众媒体之上的文娱产业所推出的明星偶像同样面临新的变化。尤其是在扁平化趋势明显的社交媒体中,节点化的个体用户存在链条囊括了所有在其平台上活动的角色,无论是组织还是个人,明星还是素人,都成为了网状传播结构中的一个光标,一个枢纽。
在此基础上,过去由媒介技术特点所描摹出的明星光景也正在消逝,虽不足以使其成为普罗大众的一员,却也在无形中传递出某种平等对话、双向沟通的特性来。
加上虚拟空间中不再具备物理意义的围挡或其他建筑遮蔽物,公共空间与私人领域时常因为用户围观发生混乱、边界模糊。如同95后小花在片场骂人事件。本是工作场所中发生的情况,却被抛进没有任何实际空间与时间设定,没有任何前因后果的公共平台中加以凝视,自然会出现“人设崩塌”、“粉丝心态崩了”的可能。
因为这本来就是在特定情境中发生的行为,换了个情境、场所,从私人到公共场合,就容易出现崩坏。
所以我说,现在的偶像及其生活与工作领域实际上是被全面入侵的状态,技术越是嵌入于社会,这种被围观,时刻站在聚光灯下的问题就越严重。
不过,这只是让偶像经常“塌房”罢了,还未触及其行业的壁垒消解,偶像明星出现“下沉”的情况。真正使偶像成为被讽刺的208万的原因,一方面来自于其越发透明的薪酬收入和近年来频发的偷税漏税事件、社会整体经济下行与公众矛盾凸显;另一方面则反映在媒介技术正使被公开、被看见的可能性显著提高,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有机会成为万众瞩目的偶像,出演电视剧、电影,在综艺中露面。
媒介资源的扩大硬生生地将明星职业的边界扯出比原来宽广十几倍、几十倍的差距,从素人、网红,到各个领域中的公众人物,都有可能成为明星与偶像。
这就有点想新闻业了,做新闻的人多了,标准、水平自然要被木板效应里的那个最低的界限给平均掉。公众会觉得,是个人都能做新闻,都能说两嘴,对社会事件指点江山。
反过来,现在也好像谁都可以当明星、做爱豆了,动不动就赚个208万,开上豪车住上北上广的高级公寓,但工作质量却没有提升,倒是天天踩着公众的最低容忍度完成:
演戏拉胯,唱歌拉胯,综艺拉胯。
行业的职业壁垒被撕开,又被无数双脚给踏平了。这一下子,在公众这里哪还有认可度可言,哪还有职业合法性可说。
也正因如此,没有认可度,就更不可能赞同高额的收入。就这么周而复始,像个怪圈一样形成了个内娱很不健康的生态体系:
人越来越多,认可度越来越低,骂声越来越大。
好不容易出来个演技派,都要高呼一句,内娱还有救。
◼️ 愚人节的玩笑
◼️ 如何救下内娱
今天是愚人节,也是张国荣先生的忌日。
说实话我并未成为过他的粉丝,也并未深入了解过他的生平和其他信息,只看过《霸王别姬》里的他,书生气的模样,扑上脂粉,又成了另一个人,眼睛里泛光,却又沉默和寂寥。
他是个优秀的演员,敏感、细腻,善于捕捉其所扮演的人物在每一帧画面中的表情和心境。这也是为什么,他为人怀念、喜欢,在二十年后仍然被频繁提起,出现在今天热搜榜上的原因。割裂,十分割裂。
如果说对张国荣的缅怀中带着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扼腕叹息,那么这几年乌烟瘴气的内娱便为这声叹息,徒增了更为悲戚的语调。
如何救下内娱?救下这个充斥着绯闻、八卦,各种私人生活的鸡飞狗跳,粗制滥造偶像的行业?
除了重新建立起职业价值与公众认同,似乎也再别无他法。
* ᴳᴼᴼᴰ ᴺᴵᴳᴴᵀ *
♡+♡=♡²
「2024/公开课/再建巴别塔」
FIRST THOUGHT
BEST THOUGHT
追逐独立,畅意自由
♡
「2024/TuTouSuo/全程班」
将真空理想连接现实
以理想入世对抗荒谬世界